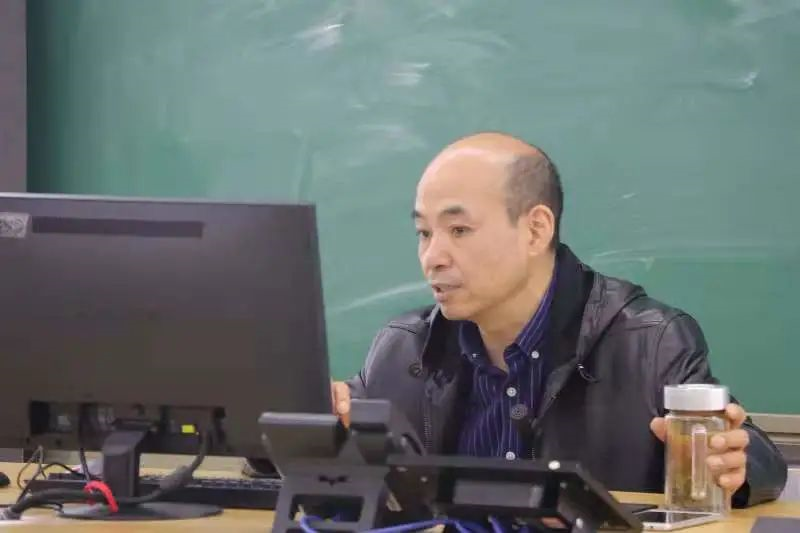
魏德勝教授分別從西北屯戍簡牘、“印”與“章”的差異、“印”“章”與印章義有關的引申義、西北屯戍簡牘的文書樣式對語言的影響及結論五個方面論述了西北屯戍簡牘中“印”“章”的用法以及西北屯戍簡牘的價值。
魏德勝教授首先對西北屯戍簡牘的發現及研究情況作了簡要介紹。西北屯戍簡牘是指西北漢長城沿線當時守邊將士留下的文書類簡牘。它以木簡為主,間有少量竹簡、帛書,主要包括敦煌簡牘和居延簡牘。西北屯戍簡牘目前共計6萬餘枚,內容主要是公私文書,另有少量典籍類簡牘,涉及漢代政治、經濟、軍事、外交、語言文字等多個方面。
在“印”與“章”的差異這一部分,魏德勝教授指出:“印”與“章”在“圖章”這個意思上為同義詞,二者在居延漢簡中均較為常用,複音詞“印章”也在此間出現。對於“章”“印”的使用,魏教授認為:(一)漢代,“章”和“印”在印章文字中的使用有明顯差異。據《漢舊儀》記,俸祿不同,“章”與“文”用於印章也有所不同,俸祿為比二千石以上稱“章”,二千石以下的稱“印”,並且在印鈕和印材方面都有嚴格規定。大量西北屯戍簡牘中引用的印章文字內容進一步證實了官員級別不同,在印章用字方面“章”與“印”的使用的確存在差異。(二)通過列舉大量簡牘及史書的內容,說明不同時代“璽”“章”“印”使用的區別。殷墟甲骨卜辭中有“印”,但詞義不是“圖章”,而是“抑”;春秋戰國時期,“印”已常被用於指代“圖章”。“璽”“印”也曾並用。關於“璽”,秦以前各種官印都可以稱“璽”,而未見私人用印章的記載;秦始皇以後,獨皇帝印稱為“璽”;在漢代,“章”開始有“圖章”義,皇帝、皇后、諸侯王稱“璽”,列侯多作“某某侯印”。此外,在“官印”“私印”等較固定的詞語中,不用“章”。這大概是因為“章”的構詞能力相對較弱的緣故。
在“印”“章”與印章義有關的引申義這一部分,魏德勝教授列舉了大量西北屯戍簡牘例證,以說明與“印”“章”有關的引申義:(一)指“封泥”。在屯戍簡中出現了“印破”“章破”的記錄,指文書傳遞過程中,偶發的封泥破損的情況。(二)“封”由動詞“封閉”義轉為名詞“封泥”義,即“封完”“封破”。同時,屯戍簡中“封”做名詞還有表示官府糧倉、府庫的封閉工具。此外,“封”還可用作量詞,如“卅井關守丞匡檄一封”。(三)印章上的文字也可以叫“印”或“章”。(四)“印”還可以做動詞,表示用印的意思。
在西北屯戍簡牘的文書樣式對語言的影響方面,魏德勝教授指出,通過“印”“章”這兩個詞的用法,可以看出政府規定對語言文字的影響。戍邊吏卒書寫文書具有一定的格式,這種文書語言可能存在背離當時實際口語的可能。如“長”,在西北屯戍簡中,既可以表示人的身高,也可用於指物品、傷口的長度;再如“高”,在屯戍簡中,它常被用於形容牲畜、建築的高度,但在睡虎地秦簡中則被用於描述人的身長。魏教授據此認為,西北屯戍簡中“長”“高”的用法應該是受到了當時文書樣式的影響。
最後,魏德勝教授作了簡要總結。他指出,傳世典籍中的用例有時不夠豐富,語料來源也並不單一,很難作為一時一地的語料使用,同時期出土文獻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這種困境;漢代屯戍簡牘作為漢代文書材料,對於研究漢代詞彙有一定的價值。

魏德勝教授的報告論證縝密,例證豐富,內容詳實,不僅提供了從出土文獻材料入手去研究詞彙的新思路,也為探索文獻資料蒐集整理的新方法帶來新啟示。
北京文獻語言與文化傳承研究基地
北京語言大學文獻語言學研究所